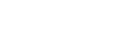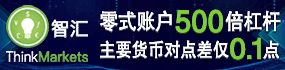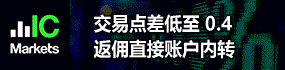[美文]在绝望中为人师表[转帖]
在绝望中为人师表
——鲜衣怒马木头 原文链接
一
绝望,这是我最近常常提到的一个词。
“绝什么来着?”来北京看我朋友正低头吃着炸酱面,闻声抬头。
“绝 ̄ ̄ ̄ ̄ ̄望!”我很严肃地重复。
他把嘴里的面条咬断,嘴巴迅速咕哝几下,清清嗓子,以手指点,用富有节奏感的欢快语调说:“丫的什么都不会,只会玩颓废!”
这句话是我们在大学时用来形容颓废派艺术青年的。只不过这一回,被形容的对象变成了我,而指代我的人称代词又变成了“丫的”。
恩,各种方言中,果然是骂人的话,最容易上口。
事实上,最早让我陷入绝望的就是北京话里以“丫的”为首的一串串骂人话。“丫的”这个词——再完整一点“丫挺的”这个词——因其发声响亮,语气铿锵,而成为我的学生们最喜欢的人称代词。上课时有人睡觉,有人想和他说话时,就要招呼他:
“醒醒嘿!丫的醒醒!”
“丫挺的干吗?”
他们一唱一和,如鱼得水。却把我一个外乡人气得几乎心肌梗塞,我不幸曾在某书看了“丫的”一词的真实含义,只要再把“丫挺的”一词语音补完,就显而易见——
丫的。
丫挺的。
丫头养的。
这无疑是老北京骂人极为阴损的一句话。未婚生子,这一个定性就轻易地侮辱了被称者本身、父亲、尤其是母亲。
我一向试图告诉我的学生们,你们多数已经十六周岁了,是要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了。所以在多数时候,我不会对他们的行为加以干涉,只是在事先提醒他们:“你确定要这么做?知道后果?你能承担?”所以,即使他们打架跷课,我也不会特别生气。但是骂人我却不能忍耐。因为第一,中国式的骂人通常都是采用迂回的方式,骂的是此人,直接侮辱的却是此人的母亲,殃及无辜;第二,被直接侮辱的此人某人的母亲却不在现场,无法还击,单方面的侵害实在卑鄙。所以,骂人在我看来是最卑劣无耻懦弱的行为。虽然,也许在漫长的语言演化中,多数人已经不知道“丫的”真正含义,但是我想,能不用还是别用了。
所以,我难得在课堂上停下讲课,说:“大家以后不要再说‘丫的’这个词了。”
“X你妈X为啥呀?”
我的脑袋里轰的一声,手里的粉笔“啪”地断了。
“……因为这是一句骂人的话。”
“我X!这也是骂人的话呀!”
和“丫挺的”并驾齐驱的,是更为直接的“X你妈X”。如果说前者是一个重要的人称代词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他们重要的语气词,既可以单独使用,表示强烈的愤慨,也可以放在句首,表示自己有话要说。因为我的做法明显会给他们的语言交流带来巨大的困绕,所以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脱口而出,用他们的句式提出了疑问。
我想限制住一句潜藏的脏话,结果却引来了如潮的直接的脏话。我想限制他们之间的侮辱,结果一瞬间,我就面对这一个班几十个人的侮辱。
那个时候,我的心跳得几乎要崩破胸腔。我最想干的,就是跳到讲台下,给这些祖国的花骨朵一人一个大嘴巴。但是我不能,因为“未成年人保护法”里有规定,因为教师不能体罚学生。
我气得不能说话,而学生在下边却是一脸茫然。我的视线在他们愚昧得近乎天真的脸上一一掠过,突然间意识到,也许对他们来说,他们真的没有考虑那些骂人的话语的真正含义,以及对别人的伤害。这倒不是说他们不懂,而是他们在以前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口不离词地这么用着,以至于他们对它们的意义已经麻木,骂人的以为没骂人,被骂的也以为没被骂,一种畸形的平衡就这样形成了。
可是现在,在这个平衡中多了一个我。我还没有习惯这些被筛掉肮脏意义的日常用语,所以他们的挠痒痒对我来说不啻是锥心之痛,他们的和风细雨对我来说不啻是电闪雷鸣。在这个时候,我面临着一个选择,这些骂人的刀子在他们的手里已经钝了,已经不起眼了,那么我应该提醒他们吗?我要把这些骂人话的原始意义再告诉他们吗?再让他们手里的刀子焕发致命的锋芒?
在下一个瞬间,我逃避了。告诉他们刀子的锋刃何在,能对别人造成怎样的伤害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每一次有意无意的挥刀我都必须用心来接着,并将我的愤怒与痛苦展示给他们看——否则不足以证明我的正确——那将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役,在这场战役中要不停表演的小丑是我,被牺牲的是我的父母的声誉。更可怕的是我知道我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习惯势力,一个年级一百多人,多数的男孩女孩嘴都不干净,与他们的对抗必然会是一个漫长、不断反复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将要承受怎样的自取其辱?我的父亲母亲,又会受到怎样无端的攻击?
“恩,没事了。想用就用吧。”
在说完这一句话的同时,无力感瞬间淹没了我的全身。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的学生错了。但是我只能这样选择。如果我坚持的话,我的学生们或许——只是或许——会拥有一个良好的语言习惯,而我,却必然——一定是必然——失去做人的尊严。
所以我逃了,让孩子们继续挥舞着他们迟钝的刀子,像做游戏一样的玩耍。
绝望,总是来源于付出代价与实际所得的巨大落差。
5楼
二
前边说过,我的学生敢于在我的面前骂人。不仅如此,他们还敢在我的面前商量放学去砍人,敢在我的办公室里抽烟,敢在我的课堂上和女朋友相互偎依耳鬓斯磨——看到这些混蛋,我只是在后悔刚走上讲台时对他们的尊重。
那时侯的想法实在是太过天真了。我的小学、初中可以说全是在较差的学校上的。所以我从小都相信,成绩绝对不是衡量一个学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职业高中毕业,每年寒假暑假,大家都会小聚一两次。他们多数已经有了几年的工作经验,在各自的岗位上——虽然是所谓的“蓝领”——都成为骨干力量。我以他们为荣,因此当我走上职业高中的讲台时,我对我的学生是信任和尊重的。
“抽烟是不好的,有害身体健康,抽烟才能刺激思维、展示魅力的说法并不足取——我就从不抽烟。但是你们都已经长大了,应该能够决定自己的行为。所以,至少,在这个学校里我不会因为看到你抽烟就给你报个处分。要不要抽?你自己决定,将来嘴臭了找不到女朋友,肺烂了活不到二十岁——不要怪我!”
“十六七岁的孩子血气方刚,受不了气,压不住火,爱打架。我知道,我也从你们这岁数过过。但是打架也分种类,一种是纯粹的意气之争,你看我一眼,眼神不对,我碰你一下,态度不好,于是就打起来了——这种架,绝对不要打,没有任何意义。还有一种是被别人欺负,或者看到有人被欺负,不得不出手——这种架打下来,我佩服你。人不是纯理性的动物,能够勇敢地保护自己,保护别人,这才是男人。”
“青春期对异性产生好感是很正常的事,所谓早恋,也算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阶段。但是喜欢一个人是不是就有资格有理由去把自己的学习彻底扔了、把父母的血汗钱乱花一气、把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当作玩笑、把自己喜欢的人烦得想跳楼——没有,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权利,所以,在你们爱慕某人时,拜托你们先想想……这场感情,对你来说到底是爱情还是游戏。在你迈出第一步之前,你有没有为将来想过。如果你们相爱了,我会祝福你们,但是如果你们为了游戏而哭天抹泪甚至寻死觅活——别让我鄙视你们好么?”
我自认为我够开放,够尊重他们的意愿。但是很快,学生们的表现就超出了我的控制。抽烟的学生在被其他老师抓住的时候,勇敢地说“是政治老师说学校不管的”;打架的学生不幸都是那些把别人的眼神当成奇耻大辱凶狠放话的混混,而真正被欺负、被榨钱的孩子却连个屁也不敢放。
至于谈恋爱的……这些高一学生在半年里,交往分手卿卿我我反目成仇的,恐怕已经超过了半数。
“老师你觉得那个女生怎么样?”
“恩?”
“漂亮么?”
“……还行。”
“那我去追她好么?够份吧?你上课别为难她啊!”
我看着这些处于所谓“花季”的孩子。他们恃勇斗狠,他们追求享乐,他们把泡美妞和钓帅凯当作学校生活里最有趣和最能显示身份的消遣。我给他们的自由,他们将之撑大了,缩小了,变成了自己最贴身的避弹衣。而对于我,他们在背后给了一个很准确的评判“傻逼”。
我突然发现我也许害了他们,我不应该给他们任何自由,也许就像刚进入学校时老教师给的告诫:“别给他们好脸色,他们不配!他们哪是人哪,根本就是一群畜生。”
最初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在心里鄙夷说这话的教师: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种老师,才会把好端端的学生变成那样。
但是现在我却在想: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学生,才会把好端端老师逼上了那样。
当我现在重整课堂纪律、禁止学生抽烟、对学生打架如临大敌、经常找学生谆谆教导的时候,同事对我的评价是进步明显,越来越像个好老师了,学生对我的尊重也增多了。但是我只觉得一阵阵的悲哀,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这种“好老师”我不愿意做。我想成为一个引导学生进步老师,而不是一个照顾学生生活的保姆,我想成为一个传授学生知识的老师,而不是一个维持纪律的狱警。
我亲爱的学生们啊,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珍惜别人对你们的尊重呢。跟你们讲理的时候你们不听,把你们当牲口来呵斥的时候,你们却唯唯诺诺了。我应得的尊重,难道只能建立在我对你们的不尊重上么?面对这样的你们,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绝望,总是产生于对美好情景的期望。
韬客外汇论坛TALKFOREX.COM
2楼
四
教完第一学期的《职业道德》我还没觉得有什么,毕竟道德是常见的、浅显的。而到了第二学期讲《法律基础》的时候,我却感到了空前的压力。毕竟不是科班出身,我对法律基础知识的认识可以说也只是一鳞半爪。过去是即使讲不好,自己还觉得有劲没使出来,还有自信,考虑到客观原因,心里也还过得去;但是现在同样讲不好,却是已经费了自己的九牛二虎之力,客观原因已经顾不上多想了,只是觉得有愧于心。
那么,如果我想把课讲好,我该怎么做?要给别人一杯水,首先自己要有一桶水。而为了这一桶水,我必须看十桶水一百桶水的法律——但是,我不是一个法律专业的学生啊,我不想当律师当法官啊,我的时间不能全投给神圣的法律啊!我对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的兴趣浓厚集中于文学、戏剧、漫画、电影……在我看来,它们中任何一个都比枯燥的法律条文有意思啊。
假设我学好了法律,接下来我要干什么?付出了这样的心血,我能容忍我的学生再不好好学习么?那么我就要纠正一百多人的学习。改变他们上课说话的毛病,改变他们只记笔记不听课的毛病,改变他们不相信书本的毛病,改变他们不求甚解的毛病——这些毛病也许跟了他们有十年了。
我,一个新人,一个没考试的副科老师,用多长的时间能够完成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个月?不可能!两个月?不可能!三个月?不可能!半年?也许……一年?也许……三年?也许……
具体多长时间我并不知道,结果我也完全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不管这段时间有多长,在这段时间中,我都将是一个疲于奔命的政治老师,而不是一个可以悠哉悠哉地考虑武侠小说会朝哪发展的网络写手,香港电影何时能走出低谷的铁杆影迷。
那时,我还是我么?
是什么时候人们把教师说成是阳光底下最伟大的职业?为什么老师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凭什么我们要在工作时间之外再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
教师只是一种职业而已,我们清贫而默默无闻,更常常被气得眼前发黑。现在还要失去自己的姓名么,而这样的牺牲,只是为了那虚无缥缈的美好未来?
曾经见到有学生家长被叫道学校来谈话,家长委屈地说:“丫挺的我是管不了了!我横丫挺的比我还横!老师您多费心,他不听话您抽丫挺的……”
看话剧《青春禁忌游戏》,里边的老师感叹说:“看看我们把学生教育成了什么样的伪君子!”
而学生则针锋相对地说:“这话应该反过来说:‘看看你们这些伪君子教育出了什么样的学生!”
呵呵,其实,绝望,它也来自于无能与自私啊。
五
在宿舍前边,有一排合抱粗的大树,顺着树干望上去,是院子上边蓝的天。
在每个班里,都有那么三四个真的喜欢学习的孩子。每天中午午休的时候,我甚至都能看到他们在专心地背单词、背课文、做习题。在我某一次因发脾气而停止讲课的时候,我看到她们无奈的眼神,在那一刹那,我决定以后不管怎样,只要我教他们一天,我都要站在讲台上把课讲完。
这些孩子,可以说是这所学校的异类。他们来到这里,只能说是中考制度的错误。或者是因为发挥失常,或者是偏科,他们的成绩未能上线,于是来到职业高中。上第一堂课时,我问他们将来的打算,其中多数说,要上自考,然后升本,然后考研。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留意着他们,半年过去了……有人已经失去了学习的尽头。
谁都不能责备这些改变的孩子。毕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学习的人……太孤单。
他们多数是腼腆得有些木讷的乖孩子,在多数人动不动就大呼小叫的班里,他们注定是容易被忽视的一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乖孩子从来吃不饱。老师的教学进度从来不是为他们考虑的,谁的成绩好注定是要被孤立的,他们想要达成自己的目标,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是别人想象不到的。
也许顽皮的孩子可以在职业高中学会重要的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但是乖孩子,却更容易莫名其妙的失去自己最宝贵的三年时间。
我现在是一个政治老师。每天,我西装革履地走上讲台,上课下课的鞠躬保持在60度以上,用最简洁的语言将本节课的内容讲完,然后在学生失去耐心之前开始讲故事。这是一个折中的办法,一方面,被故事吸引的学生勉强能够保持前十几分钟的听课效率,另一方面,我也小心翼翼地期望用优秀的故事来感染改变学生。作为一个通俗文学爱好者,我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可以讲,但是我的学生很难伺候,他们不听讲道德操守的武侠、不听讲逻辑严谨的科幻,只听鬼故事和情节线单一的奇幻。这就给我的工作增加了巨大的难度。有时我觉得我就像讲述《一千零一夜》的女孩,惊险地用故事挽救自己的性命。所不同的是,女孩的故事只要讲一遍……而我每个故事都要讲五遍……
于是,现在对我来说,多看一些情节性强、内容健康向上、又有一定文学审美价值的的奇幻故事就又成了一个任务——而关注奇幻的人可以知道这种故事是多么地可遇不可求。
但是我还在坚持着,因为我相信会有人因为这些故事而有所触动的。
无辜的孩子们,除了鼓励和关心,我甚至没有办法更多地给予你们帮助。我的政治课会考时都不需要。那么,让我给你们讲故事吧。希望在这些故事中,你们能够对文学产生兴趣,能够开拓视野成熟思维。这样的话,你们的语文成绩提高起来会容易得多的。
只有看着他们的时候,我才坚信我是一个老师。
我才欣慰地知道:绝望,是还没有摔死的人才有的权利。
(完)
3楼
三
或许我对理想,总有过分的苛求。
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就在逃避中坚持着自己的选择:我不愿意当一个为了应试教育考高分的老师,我希望能够把我的所学我的感悟真正地教给更多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接触更多,思考更多,能够体会到文学的魅力,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仍能坚持自我,相信理想。所以在应聘时,我干脆放弃了所有的普通中学,只在个大专院校、中专职高间做着选择,在我想来,这些没有升学压力的地方,应该更适合我的天性,能够让我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有更大的自己发展的空间。
来到现在的学校,从中文专业改行教政治,我倒并没有一丝怨言。
在我看来,职高的政治连会考都没有,是彻底没有压力的副科,教起来可以更随心所欲。虽然和我专业不对口,但是一般的道德、法规,翻翻书、讲一讲还是没什么困难的,要讲好,也并不困难。
但是我碰到的困难却比想象要大得多。
多数同学对道德不屑一顾。崇高、纯洁、坚定等词语在他们的眼中就是傻逼、傻逼、傻逼!他们对所谓理想的鄙视是赤裸裸的,甚至不加一点掩饰。一切的一切,好也好坏也好,他们都只用一个标准来衡量:
“值多少钱呀?”
值多少钱?我能给他们拿出多少钱?在我们这个社会上,讲求道德的人有几个是有钱人?我不知道!讲道德的人是否能够内心平静?我不知道!我们的舆论报导了很多有道德的人,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贫困潦倒——不然,哪有什么噱头可言?
但是这么一来,我这个政治老师怎么来给他们讲!要量化比较的时候,面对着社会上的声色犬马,我怎么能用早死的朱自清、闻一多、焦裕禄、赖宁去告诉他们,善有善报……诚实无价……
精神田野的荒芜,其恶性循环的后果就是,再想播种的时候……好难!
学生学会了欺善怕恶,食言而肥。有人在学校里收保护费,有人每天要给同寝的人叠被打水,有人能在说足了一节课45分钟后无辜地辩解:“我没说话呀,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说话了?老师您冤枉我!”而更多的人在校园里彼此打招呼的时候喊:“X哥!”标准流利如黑社会。
我不知道该怎样教育这些学生,对于他们,我们不能骂、不能骂打、不能开除——而事实上,如果我们这么干了,到最后被骂的、被打的很可能是我们自己。最能闹事的学生是哪些人?是那些家里已经安排好了出路的,和成绩差家里没本事的。前者事实上已经不再需要学校,后者事实上已经失去明天。成绩、毕业对他们来说都已经没有意义,像一块过期的面包失去了诱惑力。没有了欲望的他们,可以说是没有弱点的。
那么,我们所能依仗的,就只剩了语言。
语言?
用语言来教育学生,可以么?我曾经在课堂上和一个学生冲撞起来,学生兵来将挡的气势我自愧不如,在我看来明明是显而易见的结论,在学生面前变得不可思议。
“XX,别说话。”
“为什么呀?”
“现在在上课。”
“上课怎么就不能说话啊,你不是也在说吗?”
“我在讲课,你在干吗?”
“讲课不也是说话吗?你不是说话你干吗呢?放屁呢?”
“请你说话放尊重点——我是老师,你是学生,你上课说话影响别人听课。”
“学生就不是人哪?哪条法律规定学生上课不能说话了?”
这我还真不知道,再说,我就是知道,正上着课,我也“拿”不出来。所以我只好摇头叹气:“你要是再这样,咱们这课可上不下去了。”
“嘿嘿,那是你的事,别跟我扯上关系。诶,我让他别讲课了?”
“没有!”旁边马上有人搭腔。
话赶话的机智让我张口结舌。这真是一个荒谬的情景。一边是我,在尊重他人与符合逻辑规则下处处受制,另一边是学生,在以自我为中心破坏和重建规则的保护下天马行空。想来,这时候他看我,就像小鸟看蜗牛一样笨拙和可笑吧。
这个时候,我也只能无语。课后再找他谈话时,他的态度却一百八十度的转了弯。
“老师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捣乱了,我一定改!您下节课再瞧我的,我要是再捣乱,我不是人——您让我回去吧!”
我还能说什么呢?如果我还想相信他,尊重他,那么我一句话都不应该再多说。而如果我还跟他多说,那也就意味着我并不相信他的悔改,我并不相信他,尊重他——那么,我还能奢谈他对我的不尊重么?虽然他的微笑看起来是如此的厚颜无耻?
在我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坚固的堡垒,一座很难从外部攻克的堡垒,言语的力量微不足道。在城堡大门紧闭的时候,想要凭三言两语改变一个人的习惯,升华一个人的灵魂,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言语的力量是来自内部的,必须要城堡的主人先有接受的主观意愿,先把城堡大门打开,放你的语言进来才行,否则,任你舌灿莲花也是白费。就好象不同维度的空间,无法交汇,遑论作用。
一句话就改变一个人的神话,其实话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听这话的人相信这句话。
问题是,小鸟会相信蜗牛么?
我的课程,越来越简单。因为随时随地要打断进程维持课堂纪律,过去把一堂课程当成一件艺术品来完成的心已经死了——反正不管我多么卖力,一堂课被腰斩十次也会一点激情也没有了。反正没有了激情,读课本也一样吧。
所以所有的绝望,其实都来源于交流的障碍。
韬客外汇论坛TALKFOREX.COM